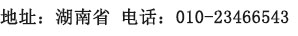交大人物:彭康校长之死
彭康,既是交通大学的最后一任校长,也是西安交通大学的首任校长。从这个意义来说,其在交通大学长校7年,交通大学西安、上海两部分各自独立为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后,在西交长校9年,直至离世。所以,写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的历史,无论如何绕不开彭康。彭康之死,成为中国教育史、西安交通大学史上一个永远的痛和伤痕。
彭康(年8月-年3月),字子劼,江西省上栗县人,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革命家。早年留学日本,就读于鹿儿岛第七高等专科学校和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系。年回国投身革命,年1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彭康是20、30年代沪上著名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先后翻译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等经典哲学著作。
年起任交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年率领交通大学内迁西安,并担任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掌校期间,交通大学经历了建国后的快速恢复和发展;为交通大学西迁和西安交通大学的建设、发展做出了历史贡献。
彭康校长带领钟兆琳等教授踏勘西安新校址
年3月,彭康遭受文化大革命迫害致死。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才得到平反昭雪。年6月24日,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交大举行了“彭康同志追悼大会及骨灰安放仪式”,由时任陕西省委书记李瑞山主持,胡耀邦等送了花圈。
在劫难逃:浩劫当中大学校长的整体蒙难。
人群一旦疯狂,往往不受控制,今天的世界是这样,比如多年前发泄对日情绪的游行忽然就演变为打砸同胞及其资产的动荡。当年的世界也是这样。“要文斗,不要武斗”虽然贵为最高指示,然而悲剧如浩浩大江无法阻挡。
运动从年5月发起。时间未久,6月1日,北大聂元梓这个混蛋就写出大字报把校长陆平揪下马来。于是,随行就市,大学陷入重灾区。有人做过统计,除了人大吴玉章、北师大陈垣、复旦陈望道、华师大孟宪承等人因年事已高实际为“挂名”校长外,其余的大学校长几乎没有例外地受到冲击:学生造反到上级定罪到群众批斗,肉体和精神遭受极大的摧残,妻子受到连累,于是有人蹲牛棚,有人自杀,有人则被杀。而在运动中被打倒最早、迫害最烈的大学校长们,活下来的基本上都成为解放最晚的人,也是文革浩劫中蒙难最深的一群人。而由于这些先生往往蒙尘在自己的学生之手,这给历史留下了极大的不堪和尴尬。让很多人终生无法释怀,永远无法自白。
自-年蒙难大学校长主要有:
年份
姓名
大学
职务
蒙难情况及结局
备注
陆平
北京大学
校长
打成黑帮,年恢复工作,任航天部长。
6月1日
蒋南翔
清华大学
校长兼高教部部长
打成黑帮,停职反省,年解放,任国家科委副主任、教育部长、中央党校副校长。
6月9-11日
贺绿汀
上海音乐学院
院长
被宣布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随之在全国性报纸上受到点名批判,遭抄家、关押、子女隔离审查。年4月7日,次女贺晓秋自杀。年1月24日,经毛泽东过问张春桥,得以获释,继续担任院长和其他社会职务。
6月10日
程今吾
北京师范大学
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实际代行校长职)
康生点名为黑帮。年病逝。
6月11日
匡亚明
南京大学
校长
批斗、撤职。年复出,担任党委书记兼校长。
6月12日
孙泱
人民大学
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实际主持工作)
江青、陈伯达污蔑其为是坏人,是苏修特务、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年10月6日,惨死于人大的地下室中。一年之后,年10月16日,妹妹孙维世因追查此事也被抓,惨死于狱中。
6月12日
彭康
西安交大
党委书记兼校长
被打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撤销一切职务。年3月28日,在游斗中被殴打致死。
6月17日
郑思群
重庆大学
校长
被市委决定停职检查。7月30日,工作组召开全校大会,宣读郑“反党反社会主义罪状”。8月2日,被强制隔离前用剃须刀割颈自杀。
6月21日
赵宗复
太原工学院
院长
被造反派批斗中从三楼坠下,当场死亡。这是目前有案可查的全国第一个自杀的大学校长。
6月21日
江隆基
兰州大学
校长
被甘肃省委在万人大会上宣布“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当日下午自杀。江隆基是党内资格最老的教育家之一,原北大校长。
6月25日
李达
武汉大学
校长
李达是中共一大代表,被湖北报纸电台点名“批判”。8月24日被湖北报纸电台点名“批判”,直接写信向毛主席求救未果,被迫害致死(一说为自杀)。
6月30日
邵凯
辽宁大学
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
被定为“三反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年1月23日,含冤去世。
6月
高芸生
北京钢铁学院
院长兼党委书记
不堪工作组和红卫兵的批斗殴打,自杀身亡。
7月6日
陈传纲
复旦大学
原副校长(已调任上海市高教局局长)
被校党委抛出,宣布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随后服大量安眠药自杀。
7月
郭影秋
人民大学
原副校长(实际代替吴玉章主持工作,刚刚调任北京新市委文教书记)
因为康生编造的二月兵变谎言,被揪回学校批斗。年3月,戚本禹在人民大学群众大会上宣布“人民大学的敌人是孙泱、郭影秋、胡锡奎。”此后长期受迫害致残,失去一条腿。年人大复校后任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
7月28日
成仿吾
山东大学
校长兼党委书记
被山东省委宣布"停职反省。10月,被《人民日报》点名。批斗中被打折三根肋骨。年8月,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批示,成仿吾离开山东大学,到中央党校专门从事马恩原著的翻译和校注工作。
8月
言慧珠
上海市戏曲学校
副校长
因连续遭批斗、殴打,写下三封绝命书后自杀身亡,死前特意换上戏装。
9月11日
常溪萍
华东师范大学
党委书记兼副校长
被聂元梓污蔑为出卖北大社教的叛徒,在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支持下,常溪萍很快被打倒。年5月25日坠楼死亡,自杀或他杀存疑。
11月
胡仁奎
北京林学院
院长
受到诬陷迫害,含冤逝世。
12月29日
陈序经
南开大学
副校长
被指控为"里通外国""特务间谍",遭批斗,突发心肌梗塞逝世。
2月16日
孟宪承
华东师范大学
校长
受到大字报攻击,猝发脑中风死去。
6月
田辛
华东化工学院
代理党委书记
受到严刑逼供,惨遭毒打,被迫害致死。年10月23日平反。
8月1日
魏思文
北京工业学院
院长
被造反派打死,成为全国第一个被打死的大学校长。
10月30日
李秋野
北京外贸学院
院长
遭到"批判斗争",自杀身亡。
6月30日
高仰云
南开大学
党委书记、副校长
被红卫兵毒打后于天津大学投湖死亡。
7月27日
李广田
云南大学
校长
文革初江青指示要打倒云南的“三家村”,李广田首当其冲。投水自杀。
11月2日
翦伯赞
北京大学
副校长
与夫人一起自杀身亡。
12月18日
因此,彭康之死,是有其历史大背景的,并且不是孤案。然而,彭康之死又有很多遗憾,一个是批斗他的人本意并不想要他死,另一个他很可能是在拖拽和抬送中被自己的风纪扣窒息死亡的。这样我们更加心痛不已。
根据当事人回忆:
另外也有关于彭康去世当天的亲历记忆:
由于年彭康去世前是我们电制63班负责看管的,而我,因缘际遇恰巧亲历了这个事件,所以有许多同学多次问我彭康校长去世的前后经过。这触痛了我本不愿回忆却抹之不去的记忆,本不想说却不得不说。
和一般同学一样,我与彭康校长并不熟悉,进校后,听高年级同学盛说他革命时的英勇故事和迁校中事实求实的作风,从而成为我崇拜的英雄。那时,交大青年学子因为有彭康这样的校长而自豪。文革开始后,运动的洪涛凶猛几至疯狂,听说彭康校长也被批斗了几次。到了68年,大多数同学逐渐看清了所谓的反修防修的斗争的真面目,厌倦了揭批斗争的无聊活动,文革初期那股狠毒与残暴劲逐渐消退。校园里已经没有运动之初那种三天两头抓人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游街的事了,彭康校长也由校革委会安排电制63班的同学给“保护”起来。参加“保护”小组的同学全是挑选出来的“红卫兵”。我出身不好,自然没有这份资格,托了组长照顾,在后期才得以挤进这支革命队伍。
为什么我要硬挤进去干那本不属自己能干的事情呢?三年级开学时,俄语老师通知我可以开第二门外语,没想到文革暴风骤雨突如其来,二外开不成了。在“复课闹革命”的时候,我想彭康校长已经没有多少事了,如果能跟着他学点日语,总比整天学毛选强。于是挤进“保护”彭康的小组。谁料人算不如天算,心强不如命强,我去了大约只有一周时间,与彭康校长话没说上一句,他就被整死了。
那是个暮春时节,本该是草长莺飞万物竞生的时节,可是冬天的寒气仍然浓厚。彭康校长被整死的那天早晨,我早早起来,见小组的同学都在睡觉,彭康校长却不见了。去问组长,组长说是交大抗校的红卫兵昨晚送来了条子,要拉彭康校长去毛主席像前请罪,今早他们来人自行拉走了。我无聊地在门外转圈,周围静静的,早起的人低头缩肩,匆匆地走过,只有两个打扫卫生的中年妇女有一下没一下地收拾着冬青树间的杂物。在那个红色恐怖的时候,气氛冷清而僵硬,全然没有现在晨练的火热场景。后来我坐在台阶上,向西边张望,希望彭康能在那里出现,让我有个与他说话的机会。
过了许久,一群人从大路上转过,急急地向这边走来。站起来,先是看到前面两个人,接着看到四个人抬着什么,后面还有几个人跟着,连走带跑,不时磕撞着路边的冬青树。到了面前,前面两个人让开,我看清了,后面的四个人抬着的原来是彭康。彭康脸朝下,四肢被四个戴红袖章的人拉着,悬空吊在那里,头无力地搭拉着,随着那四个人的脚步晃动。到了台阶前,四个人松开手,彭康被扔到地上,动也不动地瘫在那里。没有一个人出面向我说明情况,一个红卫兵扔了一句,还不老实,装死!就一窝蜂地走了。
在那个没有王法的时代,恐怕即便警察在场也只有喘大气的份,没办法的!何况我是个西贝货,自不敢出面干预。
看着他们转过冬青树,顺着大路向西走去,我急忙下台阶去拉彭康。彭康校长软得像滩泥,怎么也拉不起来。我只得跪在地上,把他的头抱起来枕在我的腿上,然后双手掐着他的腰向上扶。这时彭康校长瘦弱的身子软软的,全然吃不上力,似乎沉极了。正在无奈的时候,打扫卫生的两个妇女过来,一个人把手伸在他的鼻下试试,轻声说,死了!一时我不知是没听清,还是没反映过来,瞪着眼,傻傻地看着她,她又重复说,死了。这次我听清了,头嗡地响起来。一把把彭康校长推到地上,冲进宿舍,到组长床前,边摇晃,边喊,快起来,彭康死了!
组长听到彭康死的消息,一骨碌爬起来,随着冲到外面,看了一眼,又回到房里,急急地喊起其他的人,七手八脚地把彭康抬回去。多年后,一个同学回忆说,他起来时,看到一群人围着躺在床上的彭康校长,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大家都没有了主意。组长拨开众人,向门外冲去,边跑边喊他去找医生。
我们焦急地在房子里转来转去,不停地到门口向西张望。大家的血液仿佛凝固了,时间好像凝固了。
好不容易看到组长和一个人过来,急急地进了门。那人走到床边,拉开彭康的褂子,在那苍白的肚皮上抓了几下,肚皮上显露出一条条无法消褪的白白的条痕。这时那人急了,回过头说,快拿急救针?组长回头对我说,这个医生没想到彭康会是这个样子,他是下夜班回家顺便过来看看,没拿药。你跑去医务所要急救针,快!
我一路不停地向医务所跑去,要了急救药,又急急地冲回来,这时彭康校长身体已经冰凉了,急救针已经没有用了。我们的老校长就这样
不明不白地走了。他为革命出生入死奋斗了几十年,最后倒在了“革命”者的手中。
那是清晨发生的事,中午校学校领导就来人拿走了彭康校长早晨去请罪之前吃剩下的半块饼干和喝剩下的水,尸体也拉医院去了。
之后的几天,平静而沉闷,无聊无奈等待着。彭康校长的死讯在校园里已经流传开了,乱哄哄地流传着各样的说法。听说彭康校长的死与什么案件有关,中央对此很关心。某天,一个不愿意报姓名的同学电话中告诉我们他所看到斗争彭康校长的情况。那天,他在中心楼,看到一群人喊着口号,在电机实验室那儿推搡着彭康校长,有人在彭康校长头上打了一拳,彭康校长头就低下来,身子慢慢瘫软,这群人围上去,喊得更凶了。过了一会,人群散开,四个人抬着彭康校长向东门去了。一个在东一楼的同学也在电话中说,他看见四个红卫兵抬着彭康校长的手脚向东门走去,彭康校长的头低垂着,一步一摇,好像不行了。
彭康校长平日很注意着装,即使是挨斗的时候,衣服也穿得整整齐齐的,一身中山装,扣好每个扣子,领上的风纪扣也不忘记扣上。我们议论,也许就是这个风纪扣害了他。在他挨打后可能只是晕过去了,那帮红卫兵把他脸向下抬着,头深深低垂下,呼吸不畅,他本有患肺气肿,很可能因此窒息而死亡。
大约过了十几天,通知说要火化彭康了,让我们派个人去。谁去干这件为黑帮送丧的事?别人都是红卫兵,亲不亲阶级分,岂能干这样的事!我反正是黑五类子弟,干不干都是狗崽子,于是我主动承担了到火葬场去的任务。
火化那天,西安殡仪馆来车接人。我走之前,问王涟,在处理彭康尸体的事情上有什么想法。王涟默默想会儿,慢慢地说,他穿有一件毛衣,大概有六成新,还有那双胶鞋,也是新的。把毛衣、鞋以及袜子带回来。我一边听一边想,她不缺这些东西,可能是留下这些东西作为纪念,或是作为日后的证据。
先是到西安医学院,那是解剖彭康校长的地方。“保护”小组去了我一个,任务明确简单,去火化场取回骨灰。其他的人我都不认识,看那阴沉着面孔很威风凛凛的样子,好像是些什么领导。我跟在他们后面,进了一间阴森森的房子,里面弥漫着剌鼻的福尔马林的气味。房中间一个大台子,上面盖着白布。靠边的长长的一排矮柜子,一溜排着三个大大的玻璃瓶,里面装着肠子内脏一样的东西。一位医生模样的人过来,拉开台上的白布,对着那几位围在台子边的领导说,这是彭康。指着那三个玻璃瓶说,“内脏全部取出来了,装在这里面。”他边说边
拉开罩在彭康身上的布,露出肚皮,从下巴到小腹最下处,整个肚皮上有一条缝住的切痕。“现在肚子里装的是麦草,”他边说边用手在肚子上比划了几下。移动了几步,他指着彭康头部说,“后脑取了三条切片,保存起来了”。我站在领导们后面,觉得心阵阵收紧,面对着台上这具瘦小的尸体,一时反应不过来。心中自问,这就是彭康,这就是原来我敬佩的校长?文革前,听高年级同学讲过他的革命故事,哲学家,文学家,革命者......,这在我心目中竖起了一座神圣的丰碑。平日我见不到彭校长,但是每当学校有足球赛,就会看到他。他总坐在靠近体育馆一侧球场旁边的一张桌子后面,桌子上放着两包香烟,看着球赛,抽着烟,一根又一根。他虽然并不高大魁伟,可是,远远看去,他身上仿佛闪烁着光环,不由得赞叹道,这么瘦小的身子里,竟然蕴藏着不可估量的能量和学问,想起“仰之弥高,俯之弥深”的句子,不由得感叹,真丈夫也!现在躺在我面前的他,一只裤管被卷到膝盖,一只裤管在脚脖处向上翻着;一只脚光着,一只脚上穿着绿色的胶鞋。瘦小、苍白、干蔫,比之我在60年代困难时期所见过的路边弃尸尚且不如。房间里的人,都沉默着,静悄悄的,寂静如磐石压在人们头顶。久久,还是那位作介绍的人打破如死的寂静,说可以拉去火化了。
殡仪馆的人搬进来一个长盒子一样的东西,翻开四边,把彭康的尸体放在盒底,四边的木板竖起来,盒子成了具棺材。领导们已经退出去了,我赶紧找王涟要的衣物。在靠近柜子的地方,找着了灰灰的毛衣,卷了卷夹在腋下。一只草绿色军用胶鞋穿在脚上,自是不能脱下,另一只不知丢到哪里去了,只好放弃。
领导走了,彭康的尸体装上了车,那是辆大卡车,殡仪馆的人和我都爬上去,站在棺材盒子旁边。
汽车一路开去,我分不清东南西北,也不想问。车走了好长时间,进了一个院子。院子周围荒极了,地里密密地排列着一个个的小土堆。我想这些小土堆可能是埋骨灰的地方。
火葬场里已经有了安排,彭康来的比较迟,排在第四个。看着他们把彭康的尸体盒子放在大厅里,一时还不能进炉,我们就在那等着。
在我们前面火化的是个姓贺的。小车把他推过来,揭去盖在身上的红布,让亲属检查。看去挺福相,身下垫着厚厚的洁白的褥子,穿着一身黑呢子衣服。突然不知从哪里冲出一位姑娘,撕心裂肺地喊着爸爸,扑向躺在那里的尸体。两个人训练有素地挡住了她,她无奈地哭喊着,挣扎着,慢慢软软瘫在地上。一位像是她母亲的妇人,眼睛红红的,和几个人一起把
她搀走了。
在铁轨上行走的铁车,载着尸体进了火化炉,尸体猛地一弓,小车乘机被抽出来,尸体和身下的铁板留在炉里。炽热的火和强劲的风,舔着新被褥和呢子衣服,把它们化成了一小块一小块的(灰),飞舞着随风向上飞去,仿佛是一群黑色的蝴蝶蹁蹁起舞,伴送灵魂离开这不安宁的世界。
接下来,就轮着火化彭康了。简陋的木盒子被推过来,彭康直接被抬出来,放在小车的铁板上。敞开的上衣没有人替他掩上,卷起的裤筒一长一短依然如旧。与那姓贺的衣冠楚楚相比,这个颠倒的世界几乎一切都疯狂而无序,一位党的高级干部、哲学家、文学家、革命长者,竟然如此惨不忍睹地任人摆弄。
进了火炉,一样的一弓,一样的蝴蝶飞舞,在这里,没有级别之分,没有贫富之分,没有宠辱之分,灵魂被无常引向何处,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大约半个小时后,骨殖从炉里被扒出来,火化后的骨头保持着原来的形状,混放在铁板上冷却。工人过来问,这些骨灰用什么装?是全部带走还是只带一部分?我想骨灰不能丢失一点,应全部带回去。于是,我去前面柜台买骨灰盒,售货员听说是给彭康用,好说歹说,坚决不卖。无奈之余,请示学校。回答曰,买块布包回来。因为没有白布,只得买了块红绸布,到后面看着工人把骨殖研成骨粉,全部包起来。
殡仪馆的车把我和彭康的骨灰一起送到东大街,他们的任务完成了,剩下的事只能由我自己处理了。现在记不起是谁的指示,让我在街上买一只瓷瓶,用来装骨灰。在东大街商店(靠近新华书店,现在已经拆了)里,我看着货架上摆成一排各种各样的瓷瓶,头脑渐渐清晰,捉摸着应该买只稍微好一点的瓷瓶以慰彭康校长在天之灵,就选了最贵的一只,蓝底青点--他已经不是红色的了,还他一个清白吧!
回到学校,我把红绸子包着的骨灰、瓷瓶还有毛衣给了王涟,告诉她,鞋只剩一只,没有拿回来。她照旧没有任何表示,默默地接过东西走了。几十年过去了,彭康校长英名已经恢复,不知道王涟是否还健在,瓷瓶和毛衣是否还保留了着以使后人记住那个苦难的岁月?
彭康死后,学校通知看守人员必须提高警惕,特别要注意防范王涟自杀。我想王涟是不会自杀的。知道彭康的死讯时,她没有哭,脸上看不出喜怒哀乐,只是喃喃自语:“他走了,他走了......。”经历过革命战争九死一生的考验,多次政治运动磨练的人怎么会自杀呢?我相信她一定会咬着牙坚持到底,搞政治的人只要不死,终会有一天看到乌云褪去太阳东升的时候。可是学校的命令终是不敢违背,怎么加强防
范,成了一个难题。最后,彭康校长房里的一套围棋,使大伙来了灵感。请她来下围棋!一来可以替她解闷,分散注意力,二来也便于监视。当时,任务交给我和另一个同学承担。这真是十分尴尬的事情。王涟忍受着铭心刻骨的痛苦,不得不下楼来与她儿子一般大小的学生们下围棋;而我们打着下棋的幌子监视着刚刚失去丈夫、年龄比母亲还大的白发人。好好的一种文人逸士的高雅活动竟然成了革命的利器!这种尴尬一直继续到电制63班去上海实习才结束。
电制63班要到上海电机厂去实习。那天我拿到了去上海的火车票,收拾行李准备离开彭康住所,王涟看我收拾行李,奇怪地问我们去哪里。当她知道我们的去向后,忍不住对我说起她儿子的事。她和彭康有两个儿子,都是抗战时期在山东生的。因为经常行军打仗,居无定所,就分别送给两个农民收养。解放后,一个儿子和那个收养的农民都找不着了;另一个儿子被找到了,在上海交大上学,应该在67年毕业。可是,突然来临的文革打乱了一切,自他们当了黑帮后,两年多了,音讯断绝,死活不知。彭康死时没有掉泪的王涟,怎么也压不下母亲的天性,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虽然她说的很简单,我却听得很心酸。多年的阶级斗争,经常的划清阶级界限的压力,使我深深体会那种剜心之痛是多么辛酸难言。这就是革命?!
王涟的诉说打动了我,我问清了她儿子的名字,在校时的专业班级,答应去上海时帮她寻找。可惜,我的善良与警惕不相称,理想与能力不相称。我没有注意在我和王涟谈话时,身旁还有其他人,他告发了。当天吃过午饭,我的车票就被收走了,被留在学校,参加电机试制工作。
同学们从上海实习回来不久,开始毕业分配前的整肃工作,我被“揪”出来。我被质问的有三条,一是,为什么用红绸包彭康的骨灰;二是,为什么答应替王涟转材料(王涟曾说,彭康死前有许多话要跟组织说,我答应替她把这方面的材料转上去。事实上,她没有写过一个字,我也没有再问过);三是,为什么要为王涟找儿子。为此,我背着一袋黑材料和“不宜使用”结论进入社会,去了水库工地,
彭康死去已有40多年了,西安三兆火化场已不再是原先那样荒草凄凄,火化彭康校长时遍野的小坟堆被清理得干净,平地而起的绿树红瓦,相映生辉。不知晚上月明风清、夜深人静之时,是否可以听到枉死冤魂的长吁短叹。文革旧事已渐渐淡去,想回忆都是困难的。巴金未遂的遗愿,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因为“唯有不忘‘过去’,才能做‘未来’的主人。”巴金的想法触动了某些
人的痛处,因为“靠‘文革’获利的大有人在。”所以他的想法生前无法实现而成遗愿。想来今后,要想实现遗愿恐怕也难。
彭康校长死了,一代豪士,风流英雄,却被几双污手抓着,拽扯着,搓揉着,死得不如市井小民。豪情何在?风流何存?
愿彭康校长在天英灵原谅他的不肖弟子,他们纯净的灵魂是因被邪恶所俘虏而犯下了罪恶;愿彭康校长在天英灵法轮常转,以惨烈死亡的血为不肖弟子洗清污染了的灵魂。
彭康校长塑像
西安交大彭康书院
上海交大纪念彭康校长诞辰周年
西安交大纪念彭康校长诞辰周年报道
大约在彭康校长去世快30年的时候,在交通大学百年校庆来临之际,彭康校长的一个名章在西安交大清理楼道的过程中被发现。这是具有非常意义的一件文物。然而,我们还是要唏嘘,缘何一位政治地位如此之高的大学校长的名章会被丢进历史的缝隙之间?当时是仓促混乱中本人身上掉落,还是搜查他的物品时周转过程掉落?历史的细节不能复原,历史的伤痕即使结疤,而疤痕将永在。
如今,彭康校长已经含冤去世50年。我们只能用不断的进步来告慰前辈,特别是那些为历史错误付出牺牲和生命的人们。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